探索建筑设计文化 反思城市发展模式
01 August 20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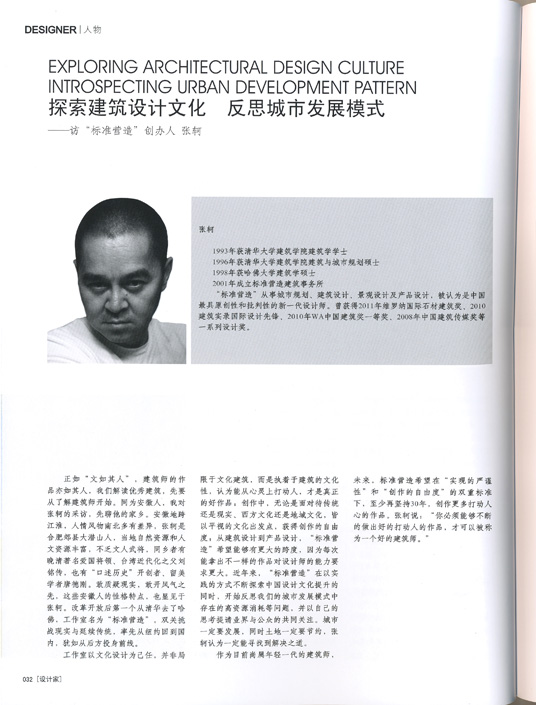





Like author,like book, the architect's work shows his style. If we want to taste the excellent architecture, we have better begin with its creator. Zhangke, an architect or from Anhui Province, has the typical Anhui characteristics. He is the first student who graduated from Qinghua Universily and went to Harvard for further study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He named his own studio "standard Architecture" which contains a meaning of inheriting the tradition and challenging reality.
The studio mainly does the design in cultural aspect, not only design cultural architect, but focus on the culture behind the construction, He thinks that the real excellent work can move others from the bottom of their heart.Architects have freedom in creation, the studio treat every kind of culture equally whatever it is traditional or reality, western or territorial.
In recent years, "standard Architecture" constantly explore the way to raise the culture deposits in Chinese architecture, in the same rethink the problems such as high resource consumption in the city development pattern, The thoughts of studio arouse the attention of the public and the industry.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usage of land should be saved, Zhangke believes the solution must can be found out.
As a member of young generation architects, "standard Architecture" hopes they can persist in the two standards" Realistic rigorous" and "Creative freedom" for 30 years." If you want to become an excellent, you should create more and more moveable works."
——访“标准营造”创办人张轲
1993年获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建筑学学士
1996年获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建筑与城市规划硕士
1998年获哈佛大学建筑学硕士
2001年成立标准营造建筑事务所
“标准营造”从事城市规划、建筑设计、景观设计及产品设计,被认为是中国最具原创性和批判性的新一代设计师。曾获得2011年维罗纳国际石造建筑奖、2010建筑实录国际设计先锋、2010年WA中国建筑奖一等奖、2008年中国建筑传媒奖等一系列设计奖。
正如“文如其人”,建筑师的作品亦如其人,我们解读优秀建筑,先要从了解建筑师开始。同为安徽人,我对张轲的采访,先聊他的家乡。安徽地跨江淮,人情风物南北多有差异,张轲是合肥郊县大潜山人,当地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丰富,不乏文人武将,同乡者有晚清著名爱国将领、台湾近代化之父刘铭传,也有“口述历史”开创者、留美学者唐德刚。敢质疑现实,敢开风气之先,这些安徽人的性格特点,也显见于张轲。改革开放后第一个从清华去了哈佛,工作室名为“标准营造”,双关挑战现实与延续传统,率先从纽约回到国内,犹如从后方投身前线。
工作室以文化设计为己任,并非局限于文化建筑,而是执着于建筑的文化性,认为能从心灵上打动人,才是真正的好作品;创作中,无论是面对待传统还是现实、西方文化还是地域文化,皆以平视的文化出发点,获得创作的自由度;从建筑设计到产品设计,“标准营造”希望能够有更大的跨度,因为每次能拿出不一样的作品对设计师的能力要求更大。近年来,“标准营造”在以实践的方式不断探索中国设计文化提升的同时,开始反思我们的城市发展模式中存在的高资源消耗等问题,并以自己的思考提请业界与公众的共同关注。城市一定要发展,同时土地一定要节约,张轲认为一定能寻找到解决之道。
作为目前尚属年轻一代的建筑师,未来,标准营造希望在“实现的严谨性”和“创作的自由度”的双重标准下,至少再坚持30年,创作更多打动人心的作品。张轲说:“你必须能够不断的做出好的打动人的作品,才可以被称为一个好的建筑师。
“标准营造”,双关挑战现实与延续传统
《设计家》 :您和我差不多是同一个年代读书的,家乡也很近,当时我们那里很少有学生了解建筑学这个专业,您是怎么想到要去学建筑的呢?
张轲:我其实有点歪打正着,就是撞上了。我读高中时,社会上科学思潮很流行,我其实一直想去学物理,后来报考清华建筑系主要是受到我哥哥的影响。他当时在华中理工大学学机电,觉得建筑系的学生比较风光,加上当时清华建筑系在我们那只招一名学生,比较难考,他和别人打赌我一定能考上,就使劲诱骗我。他带我去图书馆看一些建筑的书,慢慢地我感觉到建筑和历史文化是有关联的,自己也有了兴趣,高考半年前,就决定学建筑了。进入清华,很享受学习的过程,因为之前没学过美术,第一年表现一般,第二年就比较成熟了。我在清华读完本科和硕士,直接去了哈佛。我可能是清华在改革开放之后第一个去哈佛的,之前大家可能都不敢想。
《设计家》 :据说您是自己挣够了学费去哈佛的,也就是说您读书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做设计了。
张轲:那时候读研究生接活挺容易的,而且当时清华建筑教育的特点是对于技术这种所谓的手艺的培训还不错,但对思想培训比较弱,所以我也就没什么思想上的负担,对自己没什么标准,什么都敢干,赚钱就很容易。但是反过来,这个经历对我的影响是,因为挣到过很多钱,反而觉得挣钱不是最重要的,日后不会将建筑当成一个挣钱的手段。其实大多数美国的学生,因为在学校接触的东西相对比较纯学术,然后大家觉得职业化的道路就是商业化的道路,所以毕业以后进大的商业事务所就没有什么心理负担,觉得这是必然的、应该的。但是从中国出去的像我们那一代的学生,至少有一部分人还是比较理想主义,因为在国内经历过建筑的这种商业化的疯狂,看到过金钱来得多么容易,反而是抱着更纯粹的求学心态去的。我们毕业以后反而就不再想进—些商业化的公司,或是走商业性的实践道路。
《设计家》 :您当时和伙伴选择自己创业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张轲:其实很简单,中国内地去的学生跟美国和港台学生都不一样,中国内地的学生野心比较大,给谁打工?在纽约的建筑公司都转了一圈,觉得这也很烂那也很烂,没有一个看得上的,所以就自己干。当时在美国的同学说,在纽约呆着,觉得对自己的未来特别可预见,因为美国建筑业的系统已经很完善了,大家都可以按部就班,你知道30年后自己就关在那个玻璃小屋里面,这种可预见的无趣性是生命无法承受的。而中国的建筑业有这么多的不可预见性,也就更有挑战性。我有时候常说,在纽约的时候大家都在纸上谈兵说我要去中国,多好,但大家都是只说不练,不愿意下决心回来。就像那时候中国是战场,没有一个敢上战场的。我是最先回来的,这可能和我是安徽人有关系,安徽人的性格就比较猛一点,说回来就回来了。
《设计家》 :您是在2001年因为明长城遗址公园设计竞赛的契机回到国内的,能和我们谈谈这个项目吗?
张轲:其实这是一个偏艺术的国际设计竞赛,其性质既算旧城保护,也是城市景观,还有建筑的成分。我们也比较幸运,是评委一致全票入选的第一名。其实这是一个态度问题,其他参赛者都过于想表现一定要怎样做一个新的城墙,而我们认为这个城墙遗址公园的意义在于更真实地呈现历史本来的状态,就是它所表现的历史的层次。我们是唯一建议对城墙不做任何修饰的参赛单位,而是对周边一些旧的院落、景观进行保护,我们自己爬城墙,对所有的古树进行测绘并保留下来,其实做的是很细致的也很现实的工作。
《设计家》 :您与团队为何将工作室命名为“标准营造”?是希望成为一种标准还是希望符合某种标准?“标准营造”这个名字所表现出的模式感和你们强调的“建筑文化”的抽象性之间有没有矛盾?
张轲:我觉得你们问的这个问题还挺有意思。其实“标准营造”这个名字,表达了我们一直以来对现状很不满的情绪。因为建筑这个行业有太多的让人很无奈的标准,或者说是伪标准,我们因为是年轻一代,就希望来挑战现状,挑战标准。实际的意义是以自我为标准,就是说你不要再来告诉我什么是标准,我们自己就是,其实有不断地挑战建筑更本质问题的意思。我们一直都是在挑战现有的标准,包括自己创造的任何事物。其实我们做的建筑一点都不标准,都是反着标准干的。我觉得“标准”从文字意义上很有意思,它看上去很中性,不代表任何固定的建筑风格,反而更有创新的力量。
《设计家》 :您曾谈到,工作室以文化设计为己任。这种对文化的追求,怎样与您对“营造”的思考与探索相融合?又怎样影响您在具体项目中的思路?
张轲:我们一开始并没有说一定只做文化建筑,我们强调建筑的文化性,其实不是说博物馆就是有文化的,有足够多的博物馆被做得没有文化。
《设计家》 :而像你们做的阳朔的商业街也很有文化性。
张轲:对,一个小街坊、街道也可以体现—种文化的延续性,都是当代文化的一个方面。包括你们对和名称有关的“营造与文化”的提问,一开始“营造”这两个字大家都听不懂,什么是标准营造?营造是文化的一种延续。中国在新文化运动之前,是没有“建筑”这个词的,都是用“营造”,包括以前的施工队叫“营造场”,可能“营造”包含更多的创作意义和空间意义。而“建筑”在我的理解里更多的是指物体,当然这个词是从日本过来的,日本当时是受西方影响的。所以我觉得“标准营造”有挑战的意义也有延续的意义。
文化平视下的创作自由
《设计家》 :你们关于一个好的建筑的标准是什么?
张轲:我其实没有想过这个问题。现在太多的建筑想去迎合大众的感官,但我们其实一直比较关注的是,建筑在打动人的感官和身体的同时,是不是也可以同时打动人的思想和精神层面。其实刺激感官是很容易的,但我觉得作品是不是能够从心灵上打动人,这是我们追求的一个目标。
“标准营造”有一些建筑,从视觉上给人的冲击力也还挺不错,但是大家仔细思考的时候可以有更深的理解——对于不同地域文化的理解,对于建筑当代性的理解,这是我们希望能够不断地去实现的。这是我们自己的标准。
《设计家》 :您如何评价当今这个时代的大众感官趣味?
张轲:大众趣味永远是最容易满足的。当下大众趣味表现出的有些问题,所谓浮浅、庸俗,这是每种文化在物质问题突然刚解决的时候都会出现的,至少我们应该看到,我们的文化毫无疑问处于一个上升的阶段。因为已经没有办法再下降了,已经跌倒谷底了,所以我没有那么悲观。
《设计家》 :近年来,专业媒体对标准营造的作品评价都很高,你们如何看待来自大众层面的评价?
张轲:之前的十年里,我们可能比较清高吧,多数时候只选择在专业媒体发表作品,现在可能是时代不一样了,大家对建筑的关注比较多,但是我们还是坚持首先要得到专业媒体的认可,这是我们的标准。而大众媒体,是会靠时间来逐渐认识的。我更希望50年以后,也许大家觉得中国在今天这个时代其实有很好的建筑师。
《设计家》 :所以我觉得建筑这件事,本身是有挺多矛盾的,一方面建筑的使用者是大众,但是建筑师更在乎的是专业界对他作品的评价而不是大众,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张轲:我觉得首先使用者的评价高于专业的评价。因为建筑作为一个创作的媒体,真正使用者的体验和理解是第一位的,专业媒体的评价应该建立在使用者的评价基础上。当然我们要分清公众作为使用者和大众媒体的趣味这是两件事,这就牵涉到建筑好不好用,这是必须要解决的问题。所以从这个角度说,我觉得没有矛盾。
《设计家》 :标准营造近年来比较令人关注的作品可能是在西部的一些公共用途的建筑,谈谈你们是因为怎么样的机缘接触到这类项目?
张轲:建筑师这个职业有趣和无趣的地方都在于它的不可预见性很强,很难说能完全主动地选择项目,除非你是做特定类型的商业建筑。我们所有的项目都是有一些机缘在里面,当然这个机缘里有自我的兴趣点和选择。其实我们的项目,包括西藏的项目,都还不错,跟合作者(我们一般不叫甲方)的价值观有重合点。我们西藏的合作者欧阳旭,就一直是很有人文理想的,他北大中文系毕业,在西藏前后呆了十几年。我们一块在西藏的大峡谷走徒步,其实开始我也只是比较在意这个徒步而已,一块走了几天,他就说这个事我们就给你做了。
《设计家》 :您的这些项目,使用者对它们的评价如何?
张轲:当然我说这话不合适,但是确实是大多数人去了之后都会有惊喜吧,觉得没有想到在这里会有这样的建筑——它有和土地相连的生长感,但是你又能很明确地理解到它是当代的建筑。包括国外的一些媒体也是挺吃惊,大家没有想到中国能有这样的建筑出现。
《设计家》 :众所周知,西藏是地域民族传统文化比较强的地方,而您希望做当代建筑,在地域文化和建筑的当代性之间,如何掌握这个平衡?
张轲:其实我觉得挑战更大,比在城市里面做建筑的压力更大。因为当地文化对你有一种很强的期待,就是如何具象地表现这种文化,其实压力是很大的。当时我们也犹豫了很久,要不要接这样的项目,但是我们后来一想,如果我们不去做的话被毁的可能性更大。总的来说是一个态度问题,就是说要有—个文化平视的态度。当你到了—个自身文化根源很深的地方,很容易就是仰视、拜倒在她的脚下,然后你只有模仿和拷贝的可能性。还有一种态度就是无知的傲慢,觉得我们永远比他们强,觉得我们很先进,然后我们要教他们做什么。所以当你既不仰视也不俯视的时候,表现的是一种真正的尊重,你可以和藏族的朋友很自由地开放地辩论,但最终大家是平等的。因为你有平视的文化出发点 所以你有创作的自由度,所以你觉得西藏文化也需要有当代的建筑出现,而不是永远把它藏在博物馆里,说建筑永远都只能像100年前那样做。其实返回到中国当代的建筑,也是一样的道理。
探索设计文化,反思城市发展模式
《设计家》 :你们现在主要的工作有哪些?
张轲:我们做很多跨界的设计。我们的建筑项目地域和类型跨度都非常大,有远在西部的旅游类项目,也有在上海这样东部沿海城市的博物馆和汽车研发基地,很多项目也是将景观和建筑融合在一起来做的。当然,我们也一直在做家具设计,今年的米兰设计周上,我和中国家具品牌锐驰合作了—个叫“山居”的概念家具装置艺术;意大利的顶级家具品牌Moroso也第一次请中国设计师设计产品,还有几个建筑师也做了,我的作品是名为“隐龙”(Hidden Dragon)的红色沙发。未来建筑和产品设计一定是朝多元化方向发展的,建筑设计和产品设计之间有非常多的延续性,因为产品设计也有一个传承和原创的要求。如今,产品设计美学和建筑设计美学之间互相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包括像苹果这样的产品美学,已经非常直接地影响到了建筑设计——这个世界越来越复杂,那种简洁和朴素,是建筑师最难做到的一件事情。
《设计家》 :标准营造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了对文化身份独立性的强调,具体表现在建筑文化上,您认为工作室给这个时代的中国建筑文化带来了哪些探索与成果?
张轲:作为中国年轻一代的建筑师(十年内还可以叫年轻一代),当然从建筑文化上,我们希望自己以实践的方式来带来一些不同的探索。我觉得中国建筑,首先要拒绝模仿,目前有些大院和商业事务所,仍然是不以模仿为耻辱,我觉得这种文化必须改变。
《设计家》 :中国现在也越来越多地出现独立事务所或者独立建筑师,您怎么看待这个群体?
张轲:我觉得如果除去那些假冒的以外,真正独立的也是越来越多了,这是一件非常大的好事。经常有人把中国现代的这些建筑师和日本相比,我们总体上比他们差了好几代,日本将优秀的独立建筑师尊称为建筑家,当中国被叫做建筑家的群体真正多起来,而且整体建设速度逐渐慢下来的时候,可能中国总体的建筑会真正得到世界更多的尊重。
但是我觉得中国城市化过程中所需要思考的不仅仅是设计创作的水平问题,其实我们更需要反思城市发展模式的司题。从规划角度,我们的城市仍然是在高资源消耗前提下的爆炸性发展,包括土地资源的消耗,当这种规划方式成为了一种习惯,这是很糟糕的事情。现在很多大的规划院、景观设计院,干的都是快速生产的“行活”,作为创作型事务所,我们需要更多地思考一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模式,包括节约土地的问题。
我们在2011年成都双年展上提出的“村庄工体化”概念,其实不是说可以解决这些问题,而是提请所有城市规划者和建筑师都来考虑城市扩张中节约土地的问题。城市必须发展,同时土地必须节约,有什么解决办法?肯定有的.只不过之前我们没有提出这样的问题。
我觉得建筑师应该还是更像导演,导演分两类,一类就是每次做出来的片子都很类似,还有一类就是每次出来的片子跟之前的都不是一个类型,但是也很棒。我们是希望在创作上能够有更大的跨度,这方面我们还是挺自信的,因为每次做不一样的东西对你的能力要求更大了。
在原创性与严谨性双重标准下创作更多打动人心的作品
《设计家》 :您谈几个重要的作品吧。
张轲:建筑作品中,作为第一个建成的房子,北京的武夷小学礼堂看上去也很有激情,还有对整个行业不满的情绪,同时也提出了中国建筑当代化的问题。当然西藏的建筑是另外一个探索——在不同的文化领域。包括将来我们在国外做建筑,都需要对当地文化有平视的尊重,同时能够很自由的自我表达,这对我们来说是比较重要的。在产品设计领域,包括米兰设计周“立体村落”装置,反映了我们对城市发展模式的思考;包括阿莱瑟的盘子,都是一些非常极简的做法,也是我们自己挺满意的。现在我们跟中国和意大利的家具和灯具品牌也在合作做一些产品设计。未来,你会看到我们更多能够打动人心的作品。标准营造会同时注重真正的原创性和实现的严谨性——坚持以德国人的严谨态度来对待每一个作品,但同时又有很自由的自我实现,至少还要坚持30年吧。你必须能够不断的做出好的打动人的作品,才可以被称为一个好的建筑师,或是好的导演。
《设计家》 :我们这期的主题是“公共空间设计”,因为我们觉得,标准营造绝大部分的项目还是属于公共用途的,您能不能谈谈这一类型的建筑应该注重哪些方面的因素?
张轲:公共空间在中国是一个大家比较容易误解的概念,因为我们传统认为开放空间就是公共空间。公共空间最大的问题就是能否让城市里的人,或是使用它的人觉得这是属于我的空间,我是不是可以自由地在这个空间里进行我的表达。比如说北京之前的胡同其实是真正最好的公共空间之—,大家都把胡同当成自己的公共空间,甚至在胡同里面光着膀子下棋。—个公共空间最重要的是让大众真正的接受,而不是变成一个大家没法使用的的开放空间。我们最早设计的一个公园就在东直门下面做了一个小的公共开放空间,大家去打太极拳、跳舞,现在用得很好,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包括我们在西藏做的雅鲁藏布江小码头,当地的藏族人谈恋爱也到那边去坐坐,他们觉得是属于他的公共空间。当然最大的公共建筑比如车站,最需要考虑的是效率性。建筑最终除了使用的高效性和它的归属感之外,还有它的所谓公民性,就是对公众文化有什么贡献,它是不是传达了一些更公众的,包括是不是用最节约、节能的方式,最可持续的方式做这样的建筑,我觉得这都是当下可以探讨的一些讨论点。
《设计家》 :标准营造今后有没有一些具体的目标?
张轲:目标就是能够实现更多的打动人心的作品,坚持个30年。